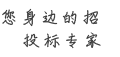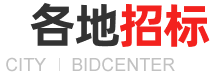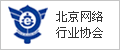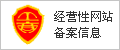眼泪是悲哀的解药
会淌眼泪的人一定是懂得这句话的意义的
——茅盾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这是茅盾12岁时写下的一生的追求和信仰。此后的人生里,茅盾始终牢记这句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奋斗了一生。

1896年,茅盾出生于浙江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望族,他原名沈雁冰。
沈雁冰刚五岁时,父亲沈永锡自己编写了一套教材来教导他,沈雁冰勤奋好学,尤其喜欢作文,这让对他寄予厚望的父母欣慰不已。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沈雁冰10岁那年,34岁的父亲竟然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陈爱珠一人挑起了全家重担。
她经营镇上一家盈利微薄的纸店,以超乎常人毅力,将两个儿子送入学堂。
而就在这时,沈雁冰便显示出了他的写作才能。
时日不久,沈雁冰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在三年的学习中,他专心研究外国文学作品,20岁那年,沈雁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此时的他突然陷入了迷茫,有点无所适从。

1920年,陈独秀把新青年建到上海,因此结识了沈雁冰。沈雁冰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成后,沈雁冰成为中共第一批58名党员之一。
1927年,沈雁冰离开商务印书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后又转任《民国日报》主编。
1930年,茅盾把这三个中篇小说《幻灭》《摇摆》《追求》合成一本《蚀》。

此后一位叫茅盾的作家开始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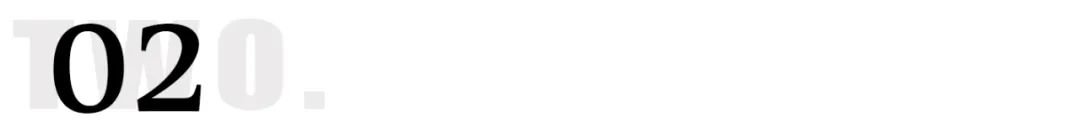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茅盾的实践活动总是和文艺运动紧密联系着的,他一方面批评封建文艺,如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培育新人。
他在30年代写的一系列作家论,如《鲁迅论》、《冰心论》、《庐隐论》、《徐志摩论》等,是以对作家作品的准确把握和评价著称的,他的《读〈呐喊〉》、《读〈倪焕之〉》等作家论,对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也作出了及时反应。茅盾是最早认识到鲁迅的意义并且给予了正确评价的批评家之一。

1978年3月1号,茅盾接受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让他撰写回忆录的要求,他开始写《我走过的道路》。
82岁高龄的他开始了紧张的生活,阅读大量资料,坚持每天写作。辛苦写作使茅盾的身体越来越弱,疲劳又使他胃口不好,营养又跟不上。

1981年2月18日,茅盾写完了小说《虹》的补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茅盾将其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 茅盾文学奖 。
1981年3月27日,茅盾悄溘然长逝,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85年历程,留给世人的,是伟大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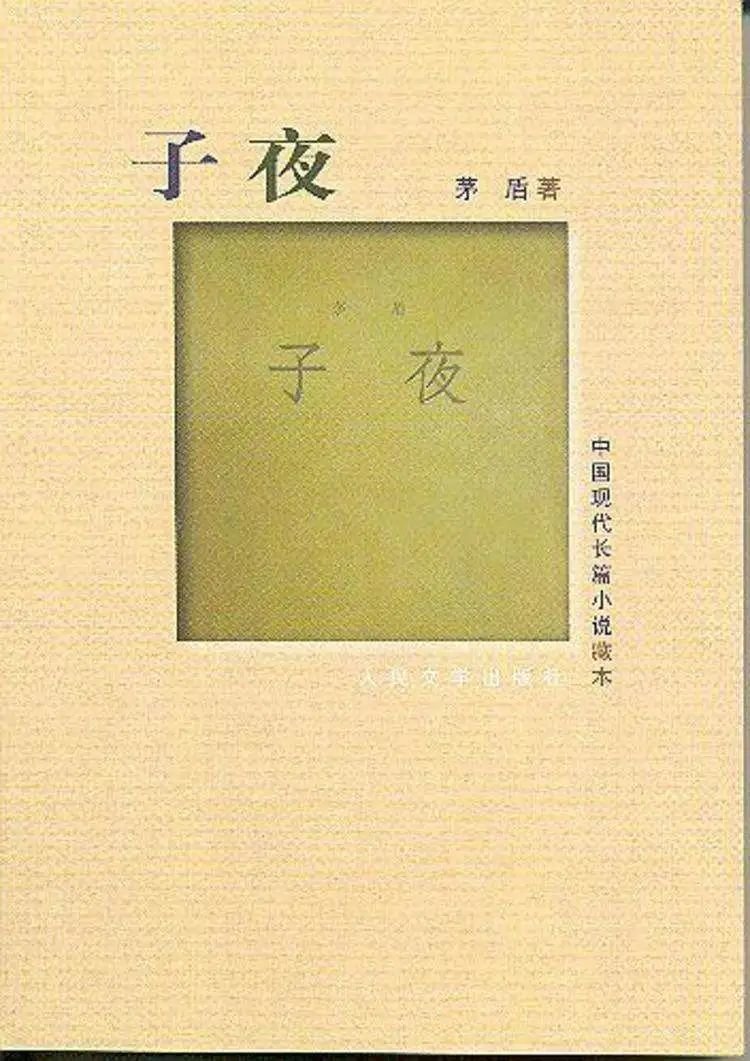
·《子夜》节选 ·
现在是午夜十二时了。工业的金融的上海人大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梦中呻吟,夜总会的酒吧 间里却响着叮叮当当的刀叉和嗤嗤的开酒瓶。吴荪甫把右手罩在酒杯上,左手支着头,无目的地看着那酒吧间里进出的人。他和王和甫两个虽然已经喝了半瓶黑葡萄酒,可是他们脸上一点也不红;那酒就好像清水,鼓动不起他们的闷沉沉的心情。并且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闷沉沉。
在铜人矿头上了岸以后,他们到徐曼丽那里胡闹了半点钟,又访过著名的秘密艳窟九十四号,出一个难题给那边的老板娘;而现在,到这夜总会里也有了半个钟头了,也推过牌九,打过宝。可是一切这些解闷的法儿都不中用!两个人都觉得胸膛里塞满了橡皮胶似的,一颗心只是粘忒忒地摆布不开;又觉得身边全长满了无形的刺棘似的,没有他们的路。尤其使他们难受的,是他们那很会出计策的脑筋也像被什么东西胶住了——简直像是死了;只有强烈的刺激稍稍能够拨动一下,但也只是一下。
“唉!浑身没有劲儿!”
吴荪甫自言自语地拿起酒杯来喝了一口,眼睛仍旧迷惘地望着酒吧间里憧憧往来的人影。
“提不起劲儿,吁!总有五六天了,提不起劲儿!”
王和甫打一个呵欠应着。他们两个人的眼光接触了一下,随即又分开,各自继续他们那无目标的了望。他们那两句话在空间消失了。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好像不是自己在说,自己在听;他们的意识界是绝对的空白!
忽然三四个人簇拥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嚷嚷笑笑进来,从吴荪甫他们桌子边跑过,一阵风似的往酒吧间的后面去了。吴荪甫他们俩麻痹的神经上骤然受了一针似的!两个人的眼光碰在一处了,嘴角上都露出苦笑来。吴荪甫仍旧自言自语地说:
“那不是么?好像是老赵!”
“老赵!”
王和甫回声似的应了两个字,本能地向酒吧间的后进望了一眼。同时他又本能地问道:
“那几个又是谁呢?”
“没有看清。总之是没有尚仲礼这老头子。”
“好像内中一个戴眼镜的就是——哦,记起来了,是常到你公馆里的李玉亭!”
“是他么?嘿,嘿!”
吴荪甫轻声笑了起来,又拿起酒杯来喝了一口。可是一个戴眼镜的人从里边跑出来了,直走到吴荪甫他们桌子前,正是李玉亭。他是特地来招呼这两位老板。王和甫哈哈笑道:
“说起曹操,曹操就到,怎么你们大学教授也逛夜总会来了?明天我登你的报!”
“哦,哦,秋律师拉我来的。你们见着他么?”
“没有。可是我们看见老赵,同你一块儿进来。”
吴荪甫这话也不过是顺口扯扯,不料李玉亭的耳根上立刻红起了一个圈。仿佛女人偷汉子被本夫撞见了那样的忸怩不安也在他心头浮了起来。他勉强笑了一笑,找出话来说道:
“听说要迁都到杭州去呢!也许是谣言,然而外场盛传;你们没有听到么?”
吴荪甫他们俩都摇头,心里却是异样的味儿,有点高兴,又有点忧闷。李玉亭又接着说下去:
“北方要组织政府,这里又有迁都杭州的风声,这就是两边都不肯和,都要打到底,分个胜败!荪甫,战事要延长呢!说不定是一年半载!民国以来,要算这一次的战事最厉害了;动员的人数,迁延的时日,都是空前的!战线也长,中部几省都卷进了旋涡!并且共匪又到处扰乱。大局是真正可以悲观!”
“过一天,算一天!”
王和甫叹一口气说,他这样颓丧是向来没有的。李玉亭听着很难受,转眼去看吴荪甫,那又是惶惑而且焦灼的一张脸。这也是李玉亭从来不曾见过的。李玉亭忍不住也叹一口气,再找出话来消释那难堪的阴霾:
“可是近来公债市场倒立稳了,没有大跌风;可见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时局前途还乐观呀!”
“哈哈!不错!”
吴荪甫突然狞笑着说,对王和甫使了个眼色。王和甫还没理会到,李玉亭却先看明白了;他立刻悟到自己无意中又闯了祸,触着了吴荪甫他们的隐痛了。他赶快一阵干笑混了过去,再拿秋律师做题目,转换谈话的方向:
“南市倒了一家钱庄,亏空四十多万;存款占五分之四。现在存户方面公请秋律师代表打官司。荪甫,令亲范博文也吃着了这笔倒账!近来他不做诗,研究民诉法了。听说那钱庄也是伤在做公债!”
吴荪甫点着头微笑,他是笑范博文吃着了倒账这才去研究法律。王和甫淡淡地说:
“没有人破产,那里会有人发财!顶倒霉的是那些零星存户!”
“可不是!我就觉得近年来上海金融业的发达不是正气的好现象。工业发达才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正轨!然而近来上海的工业真是江河日下。就拿奢侈品的卷烟工业来说,也不见得好;这两三年内,上海新开的卷烟厂,实在不算少,可是营业上到底不及洋商。况且也受了战事影响。牌子最老,资本最大的一家中国烟草公司也要把上海的制造厂暂时停工了。奢侈品工业尚且如此!”
李玉亭不胜感慨似的发了一篇议论,站起身来想走了。忽然又弯了腰,把嘴靠在吴荪甫耳朵边,轻声说道:
“老赵有一个大计划,想找你商量,就过去谈谈好么?那边比这里清静些。”
吴荪甫怔住了,一时间竟没有回答。李玉亭格格地笑着,似乎说“你斟酌罢”,就转身走了。
望着李玉亭的背影。吴荪甫怔怔地沉入了冥想。他猜不透赵伯韬来打招呼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李玉亭又是那么鬼鬼崇崇,好像要避过了王和甫?他转脸看了王和甫一眼,就决定要去看看老赵有什么把戏。
“和甫,刚才李玉亭说老赵有话找我们商量,我们去谈谈罢。”
“哦,——就是你去罢!我到那里去看一路宝。老赵是想学拿破仑,打了一个胜仗,就提出外交公文来了!”
两个人对看着哈哈笑起来,觉得心头的沉闷暂时减轻了一些了。
于是吴荪甫一个人去会老赵;在墙角的一张小圆桌旁边和赵伯韬对面坐定了后,努力装出镇静的微笑来。自从前次“合作”以后,一个多月来,这两个人虽然在应酬场中见过好多趟,都不过随便敷衍几句,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面开始密谈了。赵伯韬仍然是那种很爽快的兴高采烈的态度,说话不兜圈子,劈头就从已往的各种纠纷上表示了他自己的优越:
“荪甫,我们现在应得说几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的旧账可以一笔勾销!可是,有几件事,我不能不先对你声明一下:第一,银团托辣斯,我是有份的,我们有一个整计划;可是我们一不拒绝人家来合作,二不肯见食就吞;我们并没想过要用全力来对付你,我们并不注意缫丝工业;荪甫,那是你自己太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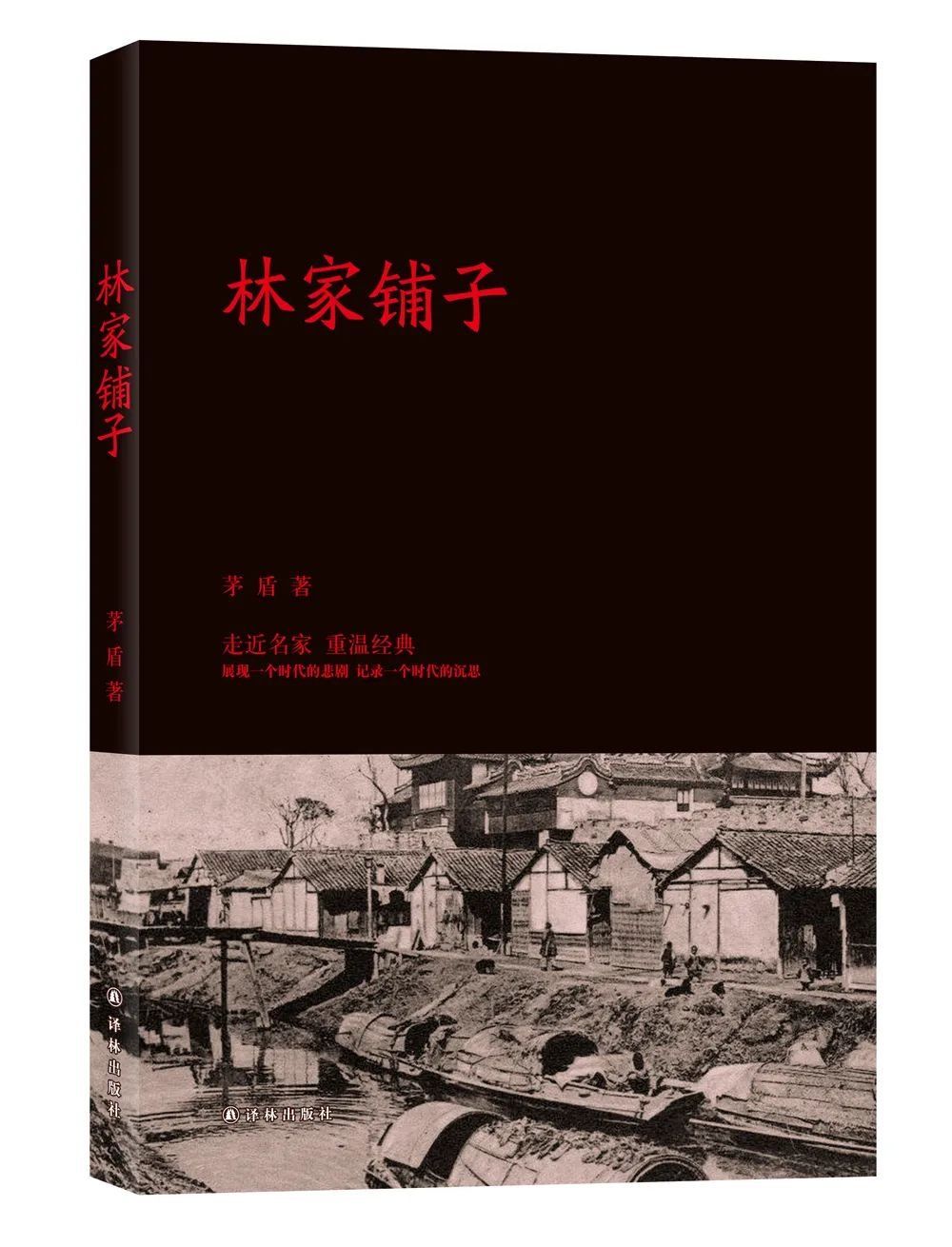
·《林家铺子》节选 ·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掼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很听得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 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 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 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 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 呃——”
“妈呀! 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 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比爱那小花更甚。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嗳,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有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儿,不能不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像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么? 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那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 那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 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里。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 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 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钥匙! 咳! 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钉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项圈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 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呃——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七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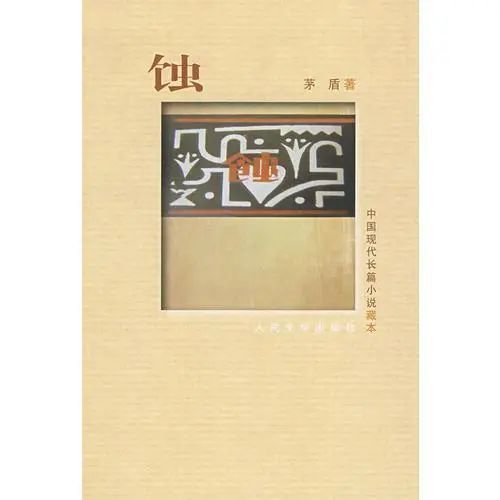
·《蚀》节选 ·
S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五卅”周年纪念会去了——几乎是全体,但也有临时规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静女士。学校中对于他俩的关系,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种种猜度和流言,这固然因为他们两个人近来过从甚密,但大半还是抱素自己对男同学泄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听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恋爱的冒险的断片以后,总是闭目摇头,像是讽刺,又像是不介意,说道:“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这个“理性人”——同学们公送他的绰号——本来常说世界万事皆小说,但他说抱素的自述是小说,则颇有怀疑的意味。可是其余的同学都相信抱素和静的关系确已超过了寻常的友谊,反以李的态度为妒忌,特别是有人看见抱素和静女士同看影戏以后,更加证实了;因为静女士从没和男同学看过影戏,据精密调查的结果。
现在这“五卅”纪念日,抱素和静女士又被发见在P影戏院里。还有个青年女子——弯弯的秀眉,清澈的小眼睛,并且颊上有笑涡的,也在一起。
这女士就是我们熟识的慧女士,住在静那里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职业还没把握。她搬到静处的第二日,就遇见了抱素,又是来“报告消息”的。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旧的洋服;血红的领结——他喜欢用红领带,据说他是有理由地喜欢用红领带——衬着他那张苍白的脸儿,乱蓬蓬的长头发,和两道剑眉,就颇有些英俊气概,至少确已给慧女士一个印象——这男子似乎尚不讨厌。在抱素方面呢,自然也觉得这位女性是惹人注意的。当静女士给两人介绍过以后,抱素忙把这两天内有不少同学因为在马路上演讲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被捕的消息,用极动听的口吻,报告了两位女士,末了还附着批评道:“这些运动,我们是反对的;空口说白话,有什么意思,徒然使西牢里多几个犯人!况且,听说被捕的‘志士’们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认是来讲演的,实在太怯,反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说到最后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胜愤慨的神气。
静是照例地不参加意见,慧却极表同情;这一对初相识的人儿便开始热闹地谈起来,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后,静的二房东便常见这惹眼的红领带,在最近四五天内,几乎是一天两次。并且静女士竟也破例出去看影戏;因为慧女士乐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静同去。
这天,他们三个人特到P影戏院,专为瞻仰著名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在静女士的意思,以为“五卅”日到外国人办的影戏院去未免“外惭清议”,然而终究拗不过慧的热心和抱素的鼓动。影片演映过一半,休息的十分钟内,场里的电灯齐明,我们看得见他们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静居中。五月末的天气已经很暖,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伏在弯弯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庞对照,越显得晶莹;小嘴唇包在匀整的细白牙齿外面,像一朵盛开的花。慧小姐委实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说静女士不美。慧的美丽是可以描写的,静的美丽是不能描写的;你不能指出静女士面庞上身体上的哪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腊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点,肉感的特点;你竟可以说静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凑合为“静女士”,就立刻变而为神奇了;似乎有一样不可得见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了她的肢骸,布满在她的百窍,而结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个的美。慧使你兴奋,她有一种摄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地只往她旁边挨;然而紧跟着兴奋而来的却是疲劳麻木,那时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而如果有一千个美人在这里任凭你挑选时,你一定会奔就静女士那样的女子,那时,她的幽丽能熨贴你的紧张的神经,她使你陶醉,似乎从她身上有一种幽香发泄出来,有一种电波放射出来,愈久愈有力,你终于受了包围,只好“缴械静候处分”了。
但是现在静女士和慧并坐着,却显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那时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学们都说是为了静,但他自己觉得多半是已变做为了慧了。只不过是一个“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摄引力的!有时他感得在慧身边虽极快意,然而有若受了什么威胁,一种窒息,一种过度的刺激,不如和静相对时那样甜蜜舒泰,但是他下意识地只是向着慧。
嘈杂的人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腾起,布满了全场;人人都乘此十分钟松一松过去一小时内压紧的情绪。慧看见坐在她前排斜右的一对男女谈的正忙,那男子很面熟,但因他低了头向女的一边,看不清是谁。
“一切罪恶都是环境逼成的,”慧透了一口气,回眸对抱素说。
“所以我对于犯罪者有同情。”抱素从静女士的颈脖后伸过头来,像预有准备似的回答。“所以国人皆曰可杀的恶人,未必真是穷凶极恶!所以一个人失足做了错事,堕落,总是可怜,不是可恨。”接着也叹息似的吐了一口气。
“据这么说,‘罚’的意义在哪里呢?”静女士微向前俯,斜转了头,插进这一句话;大概颈后的咻咻然的热气也使她颇觉不耐了。
抱素和慧都怔住了。
“如果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是你们的意见,他为什么写少年赖斯柯尼考夫是慎重考虑,认为杀人而救人是合理的,然后下手杀那个老妪呢?为什么那少年暗杀人后又受良心的责备呢?”静说明她的意见。
“哦……但,但这便是陀氏思想的未彻底处,所以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不是革命家!”抱素在支吾半晌之后,突然福至心灵,发见了这一警句!
“那又未免是遁辞了。”静微微一笑。
“静妹,你又来书呆子气了,何必管他作者原意,我们自己有脑,有主张,依自己的观察是如何便如何。我是承认少年赖斯柯尼考夫为救母姊的贫乏而杀老妪,拿了她的钱,是不错的。我所不明白的,他既然杀了老妪,为什么不多拿些钱呢?”慧激昂地说,再看前排的一双男女,他们还是谈的很忙。
静回眼看抱素,等待他的意见;抱素不作声,似乎他对于剧中情节尚未了了。静再说:“慧姊的话原自不错。但这少年赖斯柯尼考夫是一个什么人,很可研究。安那其呢?个人主义呢?唯物史观呢?”
慧还是不断地睃着前排的一对男女,甚至抱素也有些觉得了;慧猛然想起那男人的后影像是谁来,但又记不清到底是谁;旧事旧人在她的记忆里早是怎样地纠纷错乱了!
静新提出的问题,又给了各人发言的机会。于是“罪”与“罚”成了小小辩论会的中心问题。但在未得一致同意的结论以前,《罪与罚》又继续演映了。
在电影的继续映演中,抱素时时从静的颈后伸过头去发表他的意见,当既得慧的颔首以后,又必转而问静;但静似乎一心注在银幕上,有时不理,有时含胡地点了一下头。
等到影片映完,银幕上放出“明日请早”四个淡墨的大字,慧早已站起来,她在电灯重明的第一秒钟时,就搜看前排的一对男女,却见座位空着,他俩早已走了。这时左右前后的人都已经站起来,蠕蠕地嘈杂地移动;慧等三人夹在人堆里,出了P戏院。马路上是意外地冷静。两对印度骑巡,缓缓地,正从院前走过。戏院屋顶的三色旗,懒懒地睡着,旗竿在红的屋面画出一条极长的斜影子。一个烟纸店的伙计,倚在柜台上,捏着一张小纸在看,仿佛第一行大字是“五卅一周纪念日敬告上海市民”。
来源: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